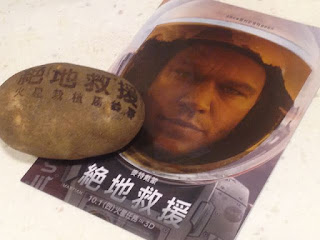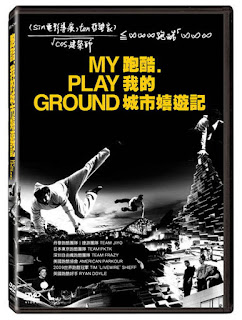由淺水灣往戰地行(林郁庭)

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,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,紅的、橘紅的、粉紅的,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,一條條,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,竄上落下,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 。流蘇想著,在這個誇張的城市裡,就是栽個跟斗,只怕也比別處痛些,心裡不由得七上八下起來。 張愛玲〈傾城之戀〉 在〈傾城之戀〉裡,白流蘇抱了破釜沈舟的決心,由滬抵港豪賭一場,誓言釣得眾人覬覦的金龜婿。她的香港初印象,無非要為心境染上各種刺激性的色彩,開戰前暗暗廝殺個沒完。從鬧區翻山越嶺到港島之南,顛簸一路的流蘇,終於見著藍綠色(而不犯沖)的海,明媚的淺水灣,主戰場。 我亦多次隨著中環出發的雙層巴士往淺水灣,穿過街市古廟、綠草如茵的跑馬地、各色人等宗教混雜的墓園,疾行於狹窄蜿蜒的濱海公路,驚心動魄處,幾要貼著山壁而行,任一窩蠻著腰肢橫不稍讓的樹枒劃頂而過,一個急轉,又像要衝出黃土崖紅土崖,掉進泛著美麗顏色的熱帶海洋。能於這般險路毫不在意高速行駛,也只有香港的大巴駕駛,個個功夫了得,讓人安穩抵達目的地時,更覺生之喜悅。 造訪淺水灣,似乎總在陰沈的午後。暴雨之後,南中國海再不見原有的藍意,翻騰濁浪盡頭,仙山一座座,漸次升起。目送渡船漸行漸遠,海天之際,一層亮似一層;日暮了,方才亮起的瞬時暗去,雲破天開那一角驀地映上一抹腥黃,殘紅盡了,一點點潛進比海更深邃的夜。 穿過夜幕向天空綻放的那朵百合,出自建築名家福斯特( Norman Foster )之手;這一頭的得獎設計,是拆了昔日的淺水灣酒店,原址上蓋起波紋狀高級公寓,挖空的心口,透出一方山的蒼綠。充滿殖民風情的二層露台餐廳和商場,仿照原酒店迎賓門面重建:穿過椰影花陰,西班牙噴泉,登上圓裙般開展的大迴旋梯,回首一望,格狀遮陽棚下的海,已籠進煙塵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