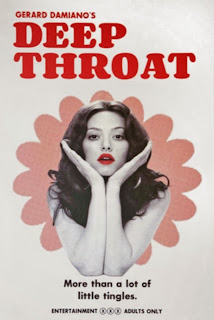雙妹雙生(林郁庭)

據說香港廣生行創辦人馮福田開業前夕,夢見天使報喜,透露如以雙姝儷影的形象經營產品,必然致富;一說馮氏於香港中區巧遇兩位少女,白衣翩翩,他心裡一動,公司品牌遂定為「雙妹嚜」( 粵語嚜頭是 商標之意,語同雙妹牌)。傳說真偽早不可考,誰有機會詢問已經作古的馮福田本人,這生意經打得可精的藥妝雜貨大亨,肯定還能提供另一版本天官賜福的神奇故事,對於走過長久歲月的品牌來說,傳奇色彩可不是愈濃厚愈好? 「要花露水嗎?這香港老品牌,到香港一定要買,別處找不到的。」藥房夥計很熱心地招呼著。那幾只細長的花露水瓶置身滿壁低矮的各色活絡油、平安膏、垃圾草油、保心安油之間,顯得有些侷促,瓶身復古的旗袍雙姝標籤,倒是跟其他充滿古早味的藥瓶盒封相處融洽。 花露水此刻擱在鋪滿參茸海味的櫃台上,等人惠顧。原始商標的兩位清裝女子縮到瓶口去了,鵝黃的玻璃樽心口透出 杭穉英繪製的月份牌局部,身裹白底印花鑲滾旗袍,翡翠珍珠長墜隨步而搖, 從無邊春色的園裡歸來的一雙儷人,捧花盈盈而笑。這個包裝比起祖母輩在老香港老上海用過的雙妹,少了幾分質樸羞澀,標榜的「復古」是以幾分現代感去烘托凸顯的,商標上驕傲地打上驗明家世的 Since 1898 ──自然是之後加上去的。